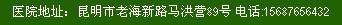|
年10月初,在龙应台客居香港大学面海的沙湾径宿舍里,二十几位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吉隆坡、香港与台北的老中青三代新闻同业,以华文媒体的未来为题,闭门盍各言尔志了十几个小时,疲劳轰炸到让人戏称被关在集中营里也不过如此。 晚上十点多,集中营打烊,曲终人散前,几位意犹未尽的新旧朋友又聚在阳台上,眺望着黑蒙蒙的一片大海闲聊,聊两岸三地传媒闲话,聊古今传媒人物,其中聊到一位是余纪中先生。 巧的是,我去香港前,《明报》副刊的马家辉请我写了篇谈台湾传媒现状的文章,在这篇题为“举目不见一个报人”刊登于我“逃离集中营”隔天的文章中,我举了两位老报人为例,其中之一正好就是余先生。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三年半前,《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过世,许多人称誉他是台湾最后的报人,并且感叹文人办报的传统从此将成绝响。当时虽曾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江山代有报人出,“余”何人也,岂无“后”乎?但从台湾这几年的报业发展来看,期待另一个报人的诞生,确实就像期待弥赛亚降临一样,永远只是个梦。 报老板能被称为报人,就像reporter能被称为journalist一样,都是角色价值的被肯定。但报人办报与非报人办报有什么不同?简单说,报人办报就是文人办报,是文人以办报的方式论政。就像张季鸾曾经说过:“中国报纸在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张季鸾当年办《大公报》是这样办,余纪忠办《中国时报》也是如此。而且这两家报纸不但都曾执报业之牛耳,有一言而动天下的影响力,更曾大赚其钱,经营上并不输商人办报。 但如果从张季鸾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来严格检验的话,余纪忠与张季鸾虽称得上是报人,却并非是完美的报人。 张季鸾虽然终身“人不隶党”,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相像,而且他还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中常委报人”这个身份,虽然让他能同时论政又问政,但这个身份终究是报人之瑕,有损报人本色。 但即使是这样不完美的报人,放眼台湾当今报业,也是百中无一,求之而不可得。 张季鸾的“四不主义”,曾经是台湾报业追求的最高价值,报纸负责人对这个最高价值,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然而现在的报业负责人,却是党、卖、私、盲四者俱全,“四不主义”早已被“四全主义”取而代之。 而且,报纸的“文人论政机关”角色日益退化,早已蜕变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实业机关”。以前,“好的报纸”、“好的新闻”(goodjournalism)就等于是“好的生意”(goodbusiness),但现在好报纸、好新闻却成了坏生意的代名词。 台湾报纸何以会变质、退化至此?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报纸与读者的角色错置。以前,报纸与读者的关系是“传媒领导大众”(thepressleadthepublic),但现在却是“大众领导传媒”(thepublicleadthepress).过去传媒决定要提供什么新闻给读者,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新闻你需要知道”(Whatnewsyouneedtoknow),但现在的标准却是“什么新闻你喜欢知道”(Whatnewsyouliketoknow)。 尤其是自香港“壹传媒”集团进驻台湾后,台湾报纸这样的质变趋势,更像大江东流一样,挡也挡不住。 也许有人不喜欢“壹传媒”,但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壹传媒”确实在短短几年内就改写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新闻史,不但改变了传媒的市场版图,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新闻的定义”。 在“壹传媒”进入台湾之前,属于隐私范围内的八卦、绯闻、丑闻,并不是不曾在台湾传媒上出现过,在两大报主宰台湾报业的时代,《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也曾经多年以争相报道极尽膻色腥能事的犯罪新闻作为竞争的手段。但依据台湾传统对新闻的定义,类似今天这样的“苹果化新闻”,不但构不成重要新闻,更上不了报纸的头版,遑论是头版头条。 现在只要“壹传媒”一爆料,台湾大小传媒无不纷纷跟进,而且无一不是以重要新闻处理,“壹传媒”俨然成为了新闻通讯社,成了其他传媒的供稿中心,也成了引领新闻风潮的龙头老大。“苹果潮”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每一间新闻办公室,每一份报纸闻起来都带一点苹果味。 当所有的传媒都以“壹传媒”对新闻的定义作为新闻的定义时,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当然就戛然而止,所谓的报人角色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张季鸾与余纪忠当年是因为《大公报》与《中国时报》的言论影响力,才逼得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蒋经国不得不买他们的账,不得不对他们以国士之礼待之,甚至不得不授以问政的权力与渠道,对他们进行“软性的收编”。 文人办报时代的报人与政治领导人的这种权力关系,虽然在骨子里仍是不对等的关系,但在形式上起码还能维持平起平坐的表相。 抗战前,蒋介石有次在南京“励志社”大宴文武百官与驻外使节的晚宴中,奉“步履长衫的小老头”张季鸾为主桌上宾,并且公开赞誉他“道德文章,名满天下”,虽然是惺惺作态,但连“凯撒”也不敢小觑报人,由此可见一斑。现在报老板与政治领导人的关系,甚至与其他更等而下之的政治人物的关系,却连形式上的平等都早已荡然无存。 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公民社会里,传媒本来应该扮演“不受国家权力控制”也“不被市场规则左右”的主体性角色,但当文人办报的传统被商人办报的现实所取代,当报老板不以追求影响力为办报的最高价值,既向国家权力屈服又对市场规则妥协时,这样的传媒其实是背叛了它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 举国尽是政客,举目不见报人,这是我们的政治现实,也是我们的传媒现实。悲乎?悲矣! 我生也晚,无缘得识张季鸾,但对他的文章他的故事,却从年轻时就略知一二,用流行语来讲,我早就是他的隔代“粉丝”。 张季鸾与蒋介石年夏天在南京“励志社”见面时,张是《大公报》总编辑,蒋是国民政府主席。“励志社”的那场晚宴虽是“中国第一报人”与“中国凯撒”蜜月期关系的缩影,但在此之前多年,凯撒与报人之间的关系其实犹如冦雠。 在跟胡政之、吴鼎昌于年接办《大公报》之前,张季鸾曾做过多年记者,而且一直是个不畏强权的记者。 年,袁世凯当总统,张季鸾在他工作的《民立报》上揭发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内幕,震动全国,但张季鸾与他的同事曹成甫当晚就被逮捕入狱。坐了三个月黑牢后,张季鸾因朋友营救而重获自由,曹成甫却已死于狱中。当时张季鸾仅仅25岁。 五年后,段祺瑞当国务总理,张季鸾又在他当总编辑的《中华新报》上,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当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内幕。段祺瑞一怒之下,不但查封了《中华新报》,也逮捕了张季鸾,把他关了半个月后才释放。 短短五年,两度对抗国家最高当权者,两度揭发政府滥权腐败内幕,两度被捕入狱,并曾一度面临被袁世凯枪决的命运,张季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记者,可想而知。 年9月1日诞生的《大公报》,就是张季鸾这种记者性格的投射。但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年,其实是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当年四月,张作霖挥军入京,立刻把他恨之入骨的《京报》老板邵飘萍逮捕。邵飘萍当时有“中国第一记者”之称,办报为文一向铁肩辣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早欲去之而后快。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罗织罪名,将他枪决。 当年八月,奉系军阀张宗昌又逮捕了《社会日报》的老板林白水。林白水在邵飘萍被杀后,仍然在报上撰文痛斥奉系军阀是洪水猛兽,张宗昌的智囊更被他形容是“终日悬挂于腿间的肾囊”。张宗昌气急败坏,效张大帅前例,也罗织了“通敌”的罪名,将林白水枪决。 但就在风声鹤唳的这一年,《大公报》登上中国新闻的舞台,而且一登台就是炮火四射。 在创报短短一年内,张季鸾曾写社评《跌霸》,痛骂独霸一时的军阀吴佩孚,“不特治军经国,有舍我其谁之叹;即谈诗说易,亦觉并世无耦。困顿经年,略物修省,而傲狠乃过于昔日”,但“综论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 他也曾写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痛斥汪精卫,“以庸才而报野心,以细人而操大炳”,而且“好为人上”,“一切问题都以适合自己便宜为标准”,“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 对当时权倾一时的蒋介石,张季鸾的抨击更是毫不留情。年在中共党史里所谓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曾无情剿杀左派人士,事后张季鸾写了一篇社评《党祸》,形容当时的社会“乖戾之气,充塞天壤;流血之祸,逼于南北”,他痛批蒋介石对共产党“爱之则加诸膝,恶之则投诸渊”,“且取缔则取缔已耳,若沪若粤,皆杀机打开,是等于自养成共产党而自杀之,无论事实上理由如何,道德上不能免其罪”。 《党祸》写完七个月后,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世纪婚礼隔天,张季鸾又写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痛骂老蒋自称“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是“浅陋无识之言”,他甚至用“兵士殉生,将帅恋爱”、“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以及“人生不平,至此极矣”这样的重话,来嘲讽蒋介石美化“革命与婚姻”的关系。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的社评,当时即轰动全国,今日读之仍是痛快淋漓。台湾现在写社评的人早已百无禁忌,但与张季鸾的“三骂”相比,火候功力高低立判。“三骂”奠定了张季鸾的报人地位,《大公报》当然也靠“三骂”建立了它第一大报的影响力。 任何当凯撒的人,都想拉拢甚至收编最有影响力的第一大报,蒋介石当然也不例外。当时传说他在办公室、官邸、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走到哪看到哪。而且他发通电给全国报馆时,开头第一句也必定是“大公报转全国各报馆钧鉴”,俨然已视《大公报》为报业龙头。至于约见张季鸾“垂询”国事这种“礼贤下士”的动作,蒋介石更是频繁为之,南京“励志社”那场晚宴,更曾被人以“韩信拜相,全军皆惊”这样的比喻来夸张形容。 蒋介石以国士之礼待之,当然会影响到张季鸾一向锐利的“反蒋”笔锋。再加上他的对日政策主张跟蒋介石若合符节,因此不但《大公报》的社评常给人与政府桴鼓相应的印象,张季鸾也确实偶尔扮演过君王策士的角色。 但即使如此,张季鸾仍然很努力在维持他的独立报人本色,特别是他对蒋介石处理共产党与异议知识分子的做法不敢苟同,依然大力批判。 两个较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年代,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却是最早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的报人。虽然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十分严酷,但《大公报》却敢不听党意、不从流俗,从来不以“共匪”称呼共产党,而称其为“共党”、“共军”。远赴西北边陲地区采访的《大公报》记者,更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赞美“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彻底颠覆了国民党宣传机器所塑造的“共产党是流寇土匪”的刻板印象。毛泽东曾经很感慨地对一位《大公报》记者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蒋介石对《大公报》的“附匪”言论忍无可忍,有一天终于跟张季鸾面对面摊牌。蒋虽然气得大发雷霆,但张却不惧不惊,从头到尾只是以不卑不亢的语气,反复重申“事实就是如此”,答复言简意赅,立场平和严正,十足报人风范。凯撒再霸,但又奈报人何! 第二个例子是年的“七君子事件”。张季鸾一向尊重知识分子,他在《大公报》开辟的专栏“星期论文”,曾经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左中右各党各派人士皆在其中写稿。 因此当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七人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后,张季鸾的痛心不难想象。这七个人只不过是组织了一个“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一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呼吁各党各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以及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而已,但国民政府却罗织了一份罪行完全无中生有的起诉状,企图诬陷他们。 当时各家报纸对“七君子”案件都噤若寒蝉,举国不闻异议之声。但当张季鸾得知身陷牢狱的“七君子”写了一份答辩状,逐条逐项驳斥起诉书中各项罗织的罪状后,他立即打电话给编辑部值班的同事,要求将答辩状全文立即发排,隔日登刊,而且不必送审,责任由他来负。 以今观昔,张季鸾当天的决定似乎平常至极,但在当时“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政治气氛中,举国报人却唯独张季鸾一人有此勇气。“七君子”日后全被释放,虽有许多主客观因素,但张季鸾和他的额《大公报》能无愧于报人与媒体的角色,却绝对是关键因素之一。 由于《大公报》对共产党与他们的“同路人”一向采取既不歧视也不丑化的立场,甚至常有“同情的了解”,因此共产党领导人也一样想拉拢收编《大公报》。蒋介石在南京的“励志社”奉张季鸾为上宾,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宴客时,也曾让《大公报》记者高居首席。张季鸾病危时,医院探访,但在他的病榻前,也曾出现周恩来与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各坐一侧相对无言的“和平”画面。国共两党源出一门,由此亦可见一斑。 张季鸾曾对他的接班人王芸生说过:“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这句话虽然有点老师傅叫小徒弟附耳过来交代后事的味道,本来就不想“法传六耳”,但等到王芸生撰文转述众人皆知后,师徒间这句私语却成了张季鸾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的注脚。 但相对来说,他对共产党又何尝不是如此?否则周恩来何以奉他为“报界宗师”?毛泽东又何以肯定他“功在国家”,甚至在年代末期党内整肃《大公报》时,仍称赞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应该学习的”? 张季鸾为什么能优游于国共两党之间,跟两党领导人都能保持亦友亦敌的紧张关系?是为了两边押注买保险?是心中毫无定见而投机摇摆?都不是。他之所以如此,原因非常简单: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的“四不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具体而微。他曾经形容自己和他的办报伙伴:“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治,反干涉。” 近年来研究《大公报》历史的中国大陆学者,也有许多人认为“《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这么鲜明的旗帜”。 但张季鸾并不懂复杂的自由主义理论,他只是一个“简明版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的字典里,自由主义的定义很简单:不党、不私、不盲、不卖,不求权、不求利、不求名、不畏强权、不溺富贵,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包容异己,如此而已。不论他当记者、写社论、当报老板、延揽自由派知识分子写专栏以及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他都是用行动在实践这么简单的一个信念。即使偶尔逾矩,跑到了自由主义的对面“表态”,但就像有位大陆学者所说:“他的态度是历史的态度,也是现实的态度。”比方说,他在对日抗战时的“国家中心论”主张,岁曾备受批评,更被共产党列为他政治反动的证据,却并不足以证明他背叛了自由主义。 更何况,国共两党一向视自由主义者“非我族类”,毛泽东更把自由主义者说成是“民主个人主义者”。张季鸾明知左右皆反自由主义,却依然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办报,他的信念之强、勇气之大甚至他的孤傲自负,都是不言而喻。 可惜的是,张季鸾在年才54岁就过世了。如果他能活得更长寿,活到国共内战,活到江山易主以后,《大公报》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他会不会像他的接班人王芸生在年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那样,表态“向人民阵营来投降”?他会不会让《大公报》名存实亡、苟延残喘到年才以黯然赧然的结局收场?现实的历史没有给我们答案,但张季鸾的办报历史却告诉了我们答案是什么。 也许就是因为对台湾媒体的集体不为,或者对“张季鸾精神”如烟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感慨甚至有些恐慌吧,所以我才转向美国的媒体,想从美国新闻界的历史与现实里,去寻找像张季鸾与《大公报》那样的记者、那样的报老板以及那样的媒体,既是为了替我的沮丧挫折寻求慰藉,也是为了替我的虚无麻木寻找刺激。没想到这个自私的动机,这段自我治疗的旅程,最后却写成了一本书。 在《凯撒不爱我》这本书中,我写了五十二位新闻人的故事,其中只有一篇是美国以外的故事。这些新闻人几乎都是自由派,都曾有或仍有影响力,其中多数更是跟凯撒对抗多年、被凯撒恨之入骨。这些人的名字也许跟张季鸾跟你我有别,但他们的际遇与他们的故事,却跟张季鸾跟你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能做那样的新闻人,我们呢?难道只能感叹“岂有豪情似旧时”?只能任凭“花开花落两由之”?看完这些故事后,再问问我们自己吧。 这本书先给余纪忠先生,书出之日我已重回他一手创办的《中国时报》;也献给《新新闻》每一位工作伙伴,十八年的革命感情永难忘怀;还要谢谢我的儿子泽生,这本书是他一字一句敲打出来的,也记录了我们父子一段知识性的亲情互动。 作者王健壮,于台大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与社长,博理基金会执行长。 延伸阅读: 被激情着,被燃烧着,被希望着 韩锡璋 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睛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在路上,用我心灵的歌声在路上,只为伴着我的人在路上,是我生命的远行在路上,只为温暖我的人 作为中国三个仅有的行业性节日(另两个节日是护士节、教师节),第11个记者节又一次向我们走来。 在中国大地上谱写新闻事业画卷的几十万新闻人,此时此刻,一定“心有千千结”: 很难对记者的工作特性给出一个准确定义:它是历史的记录者?生活的参与者?事件的发布者?这些都是又似乎不尽然。 在这个信息近乎以音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地球村越来越“小而密”的时代,记者的从业环境,职业使命,生存法则等等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记者的职业光环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耀眼夺目; 记者的工作生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重创; 曾经衣食无虞的纸质媒体面对来势汹汹的网络和电视已经深深感到在“风暴”中心的飘摇与莫测; 但不管如何,新闻战线和新闻人在这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他们还是被人“艳羡”的一族。 因为———他们将自己生活和社会的一部分收入历史硕大的巨囊中;他们要在遵循中国国情的情势下,高扬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让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让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他们要传递决策层的声音;他们要倾听社会的呼声;他们要正视民间的悲声;他们要弘扬生活中的真善美;他们要鞭挞黑暗角落的假恶丑;社会在剧变中,各种矛盾也在巨变中。 今天的媒体人再不是过去那种把“本报讯”、“本台消息”写好就可过悠哉悠哉日子的那份风光职业了。 她已被推上文化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接受市场的洗礼;众多媒体已不得不优先考虑生存;而遑论过舒适、滋润的日子…… 她已被当作一种没有什么特殊优势的“产业”去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一些利益链绞啮的地方,媒体有时被当作利用的工具;有时被当作攻击的“敌人”; 正常的采写受到严苛的阻碍、审查、围堵; 对方设计的圈套让你睁着眼睛往里猛跳; 此时的记者与媒体,更多领教的是“欲写新闻不自由”;遭受冷遇事小,利用司法机关某些执法者甚至黑恶势力让你品尝强权和财阀的厉害早已见怪不怪; 在转型中,在社会的角角落落,今天已不要奢望对方会给你创造什么方便条件;对方没有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地包围你、攻击你、迫害你就算“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了; 曾经的文人胸怀、书生意气、对民族与国家担当匹夫之责的豪迈与自信,在今天的媒体人身上已大大逊色; 曾经发誓以一管秃笔、满纸雄文,让山河改道、大河改向、日月低头的豪情在今天的媒体人身上还能找到多少“雪泥鸿爪”? 当个体和小团体的利益以极端自私甚至不择手段去实现时,媒体被逼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 当利益的链条将地方的新闻、宣传这些“清水衙门”也箍紧并利用时,媒体人除了失意和厄运之外,有时连困惑的权利都没有。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 崇高的职业依旧崇高;记者作为普通公民的同时,他在从业中一旦遭受不应有的惩罚和打击迫害时,我们在过去的时日里,欣喜地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及时出手“施救”; 相反,以职业的公权力去获得小团体或自身不该获得的利益时,媒体及媒体人在法治的天平上享有同等的“待遇”…… 职业使命、道德底线、从业环境的严峻挑战都构成了今天媒体和媒体人的“关键词”。 媒体的职业是清苦的,唯其耐得住寂寞,才能小有所成; 媒体的职业也存在诱惑及与之相伴而生的风险,没有高洁的人格和拥有一颗平常的心态是很难“河边不湿鞋”的。 电脑取代了笔墨;无纸化的风行已使绝大多数媒体人告别了爬格子的春雾白鬓、夏阳灼肤、秋雨蚀骨、冬风锥心的熬煎。但媒体人要想写出一则好的新闻,要想拍出一副好的图片,还得锋自磨砺出,玉乃雕琢成…… 时代呼唤更多优秀的新闻人才;时代需要更多负责任的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的的媒体;时代需要让社会的方方面面予媒体以宽容、理解、支持。 作为记者,让我们用激情拥抱自己的事业;用理性对待周围发生的事情(件);用责任肩负新闻的使命; 用作品告知和前瞻一些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故事…… 元朝时有一位擅长写梅花的尼姑,她写了一首经久不衰的梅花诗,诠释有耕耘就有收获的道理: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厉以宁也写过好多励志诗词,在此让我们选录一首一起分享和感悟耕耘与收获的甘苦。只有燃烧激情、点燃希望,才能体味、欣赏到山的巍峨、海的壮阔、雪的素洁、风的吟哦—— 林间绕,泥泞道深山雨后斜阳照溪流满,石桥短云横雾隔,岁寒春晚。返?返?返?青青草,樱桃小,渐行渐觉风光好云烟散,峰回转菜花十里,一川平坦。赶!赶!赶! 来源:年11月9日山西市场导报4--5版 倘有给山西市场导报文化副刊、太原法院文化周刊赐稿者可发这两个邮箱。如有特殊强调事宜,敬请附于稿后。 小张编辑 E-mail: qq.白癜风的治疗办法甲氧沙林溶液可以治疗白癜风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yksmz.com/zzyjg/5037.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GYMBO分享一个孩子爸爸关于小儿发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