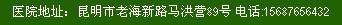|
北京中科医院是真是假 https://m.39.net/baidianfeng/a_5153160.html 据人民日报发布的《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显示,中国患抑郁症人数超过万,30%是18岁以下青少年,其中50%是在校学生。 抑郁症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名人被爆出患有抑郁症,普通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经常被抑郁症拖累。还有很多人感到悲伤、疲惫,但拿不准这是正常的情绪还是抑郁症。 如何正确认识抑郁症?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本书,它以多页的短小篇幅,简练而系统地梳理了抑郁症的概念、理论、治疗现状和文化,它还告诉你——关于抑郁症,心理学家不会告诉你的那些事。关于抑郁症,还有哪些是科学家怀疑的、误会的、不了解的?这些疑点、偏见和盲区对于抑郁症的防治,乃至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美]乔纳森·萨多斯基的《抑郁帝国》。 接下来,我们从三个部分来解读这本书。在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们是如何认识抑郁症的。在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看,抑郁症这种疾病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到底该从心理、社会,还是化学角度来理解抑郁症?这三种关于抑郁症的主流观点,作者都会介绍和评价。在第三部分,我们回归今天的日常,当今抑郁症的确诊率越来越高,抑郁症好像已经成了精神病学领域里的一个帝国。是我们真的来到了一个更加抑郁的时代,还是抑郁的概念被滥用了?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能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抑郁症,还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情绪。 至今,人类科学对抑郁症的了解仍旧还不够,我们还不清楚这种病的完整病理机制;大部分的抑郁症药物都是在其他实验中被发现有改善抑郁的副作用,然后才被投入使用的;甚至,抑郁症被写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后,手册的每一次修订都会对抑郁症相关条目进行大改。也就是说,我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仍然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而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也各不相同。 通常来说,一种疾病要想获得承认,它的症状、诊断和治疗需要尽可能地客观和普适。但是,抑郁症的症状和诊断似乎受到很大的文化影响——它在欧美的确诊率远高于其他地方,并且原因尚不明确。根据一项研究,—年,超过1/9的美国人接受过抑郁症的药物治疗,这一比例现在只会更高。你可能也发现,美剧里人们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本书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女学生叫伊菲麦露,她是个难民,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因此不能找工作,生活上困难重重。很快伊菲麦露出现了嗜睡、悲伤、社交退缩等症状。她的姑妈是一位在美国受训的心理医生,认为这是典型的抑郁症。但伊菲麦露反驳姑妈说:把生活里的一切问题归结为心理疾病,把所有的不舒服诊断为抑郁症,这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美国文化。她认为自己的情况不是生病,而是面对重大困境时的正常反应,只要拿到身份、找到工作,自然就好了。 后来,伊菲麦露的确通过改善生活状况解决了自己的心理问题。这当然不能说明,抑郁症就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疾病,但这位尼日利亚女生的确揭示了一种可能:所谓抑郁症,会不会只是欧美文化理解悲痛的一种方式? 有一个术语专门用来形容一种和文化高度绑定的精神疾病,叫作“文化制约综合征”,也叫文化束缚症候群。它指的是一系列和文化背景相关的症状,只有特定民族或地区的人会报告同时出现这些症状,有的症状甚至只在这些民族或地区出现。当地人会用这些症状命名一种疾病,但这种疾病外界并不承认。常见的文化制约综合征有马来西亚的缩阳症、韩国火病和北极歇斯底里症等等。很多学者认为,多数文化制约综合征并不是独立的疾病,而是其他问题在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特殊症状,或者根本就是一种文化习惯。 那么,抑郁症会不会是一种文化制约综合征呢? 本书作者萨多斯基的看法是:抑郁症的存在既有大量证据支持,也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受到文化制约的与其说是抑郁症,不如说是现代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对抑郁症的主流认识。 作者承认,抑郁症的命名本身就和西方历史,尤其是现代西方历史紧密相关。从古希腊到基督教的中世纪,人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命名、分析和治疗过度的忧郁。解剖学刚兴起的时候,人们更是热衷于在躯体中寻找忧郁的病灶……可以说西方的医学中还没发展出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对抑郁的研究就已经如火如荼了,甚至还有大量著作出版。只不过不同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命名和知识体系,当时“抑郁症(depression)”这个名字还不通行。 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欧洲人开始把抑郁的情绪,和人之为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正是人性高贵和敏感的体现。这种认识也是有文化背景的。举个例子,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就是这种高贵忧郁的代表。他因为父亲被害、王位被篡夺,感受到人间的丑恶而开始厌世,并对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产生了怀疑,提出“存在还是毁灭”的著名问题。哈姆雷特身上这种悲伤、沉思,又充满智慧、文采斐然的迷人状态,叫作“忧郁”(melancholy)。和忧郁相对的是哈姆雷特的女友奥菲莉娅的精神状态。奥菲莉娅同样遭受了不幸,但她被悲伤击垮,疯疯癫癫、丧失理智,这种状态被称为“抑郁”(depression)。当时的人认为,只有欧洲男性身上才会出现高贵的忧郁,女性身上只会出现病态的抑郁。至于欧洲以外的人,例如他们能接触到的非洲奴隶,根本体会不到这些复杂的忧愁。 从前的文化偏见仍然在影响着现今由欧美主导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今天,因为抑郁症就医的人仍然以女性为主,这又反过来导致了医生只能根据女性患者的症状来确定诊断标准,男性即便鼓起勇气去治疗“病态的抑郁”,也经常会被误诊。同时,很多欧美国家的研究都显示,比起白人,有色人种的抑郁症诊断更加严苛,很多医生更倾向于对有色人种作出精神分裂,而不是抑郁症的诊断。 了解的不足、标准的频繁变动、文化因素的制约和个人判断的影响……这些都在挑战抑郁症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作者认为,这些不确定性和文化的影响,在人类认识很多疾病的过程中都出现过。例如同属精神疾病的阿兹海默症,也是在确认了脑部机制之前就被承认的疾病;大名鼎鼎的肺结核更是这样。再说,即便医学没有承认,难道这种病就不存在了吗? 作者进一步指出,医学既是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共识。他援引精神病学家南西·安卓森的说法,指出整个医学史上,其实从来没有人成功找到过疾病和健康之间的界限。换言之,别说是具体的某种疾病,就是“疾病”这个范畴本身,也没有明确的定义。所以,与其往客观纯粹、边界清晰的死胡同里钻,不如更多考虑人们的需要和感受,这些需要和感受同样是真实的——虽然抑郁症的知识体系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但在很多其他族群的文化制约综合征里也能找到抑郁症的影子。古今中外,抑郁症可以有很多副面孔,比如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下沉的心、火病,甚至是一句“这个人总是想太多”……这些变形与其说是挑战了抑郁症的存在,不如说是丰富了抑郁症的内容。今天,大部分专家都承认,抑郁症不是一组单一的症状,它的症状、诊断和治疗都会受到文化影响。而作者的态度是:无论如何,命名抑郁症有助于帮助患者表达他们的痛苦。把痛苦看成一种问题,就是踏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我们来看看关于抑郁症,学界的主要分歧:抑郁症的本质是什么?是心理的、社会的,还是化学的?这也是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这个问题乍一听有一些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味道,但正是这个抽象的问题,决定了人们是否会治疗抑郁症,以及用什么方法去治疗抑郁症。同时,作者也提醒人们:对待抑郁症的本质没有必要采取非此即彼的方式,不同的治疗手段之间也不完全排斥,曾经的医学在这一点上走了弯路。 现代医学中,“心理说”的知名度最高。“心理说”的先驱是精神分析学派。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哀悼与忧郁症》中讨论了抑郁症。他认为:抑郁的根源是一个人丧失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但出于某些原因无法表达,或者不愿意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导致愤怒转向了内部。要治疗抑郁症,可以通过谈话疗法,让医生深度发掘病人的潜意识,引导他意识到自己愤怒和丧失感的真正来源,从而缓解病情。精神分析学派另一分支的代表荣格则认为抑郁症的根源是心理能量低下。心理能量为什么会低下?因为它从外部的意识世界中转移出去了,向内转化到内心的潜意识中去了。荣格认为,抑郁症患者感到缺少能量、不能集中注意力应对日常生活,其实是潜意识在告诉他:“嘿!别再对外在的事物大惊小怪,注意我,我有事情要告诉你。”荣格和弗洛伊德一样主张用谈话疗法治疗抑郁症,但他认为医师要引导患者在潜意识中发现的,不是被压抑的痛苦,而是未曾意识到的改变认知和行为模式的机会。 除了精神分析学派,现在临床上流行的另一个流派:认知行为疗法(CBT),也认为抑郁症的根源在心理。这个流派认为,抑郁的根源是患者错误的逻辑思维,比如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或者自己没办法控制生活,等等。医生可以同时从行为和思维入手,纠正这些偏颇的观念,病情自然就会缓解。 “社会说”是关于抑郁症本质的第二种观点。关于这个观点有一个很重要的争议:如果抑郁和痛苦有合理的现实社会原因,那它还算不算抑郁症呢? 很多人认为有合理原因的抑郁不算抑郁症,前面提到的尼日利亚难民学生伊菲麦露显然就是这样认为的。日常生活中总有人开玩笑说:你这不是抑郁症,是没钱没工作没有恋爱的正常反应。这个玩笑的潜台词同样是:只有缺乏合理现实原因的悲伤,才算抑郁症。 早先的精神病学同样持有这种观点。然而,随着治疗的重心逐渐向缓解症状倾斜,精神病学家逐渐改变了看法。年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认定,当一个人感到精神痛苦,哪怕这种痛苦有合理的社会原因,也不妨碍他被诊断为患有抑郁症,出于任何原因的过度悲伤都可以按照抑郁症来治疗。 一些心理学家,尤其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则开辟了另一条研究抑郁症的路径,开始寻找引发抑郁症的社会原因。 前面说到,女性的抑郁症诊断率通常高于男性,这部分是因为传统的偏见:男性的忧伤是智慧的体现,女性的忧伤则是需要治疗的疾病。此外,社会不鼓励男性表现出脆弱的情绪,让男性的抑郁症状更隐蔽,也是一个原因。除了这些,学者还观察到,社会上的歧视和性别不平等,的确让女性更频繁地陷入孤立无援、压力重重的境地,主流话语对这些痛苦轻描淡写,这就让女性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类似地,很多研究都显示,弱势群体更容易抑郁:童年时遭受过虐待的人、残疾或患病的儿童、难民和流亡者,当然还有低收入人群,都更容易得抑郁症——虽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较少遇见得抑郁症的穷人,但作者提醒:贫穷和抑郁的联系其实再自然不过了。对抑郁症进行社会分析是有意义的,因为这能帮助患者避免把所有问题归结在自己身上,也能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知道,哪些人群的抑郁情况被忽视了——生活中很少出现贫穷的抑郁症患者,可能只是他们没有时间和金钱就诊而已。 医学将抑郁症视为疾病,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刻意练习你的孩子不是学习的料错,他和
- 下一篇文章: 探索人脑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