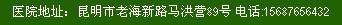|
第二章一切都在脑中?在二〇一二年,英国开立了超过五千万份抗忧郁剂处方,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数字。在该国的一些地区,例如英格兰西北部,每月平均每六个人中便有一人得到抗忧郁剂处方笺。虽然在同一时期接受心理治疗(主要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但要治疗忧郁症状,家庭医师最常见的应对措施仍是开立抗忧郁剂处方。医院开出了这么庞大的抗忧郁处方,更可看出背后在主导的意识型态和方法。自二〇一〇年以来,英国大幅删减「以社区为基础的替代方案」,更加强化此意识型态与方法,即将忧郁视为需要采取医疗措施的疾病,当中也包括从焦虑到思觉失调症由轻到重的各种精神状况。这种观念通常被称为「医学模式」,自十九世纪以来形塑了我们对健康和精神痛苦的理解。约翰?哈里斯和怀特定义了医学模式,他们强调:身体被看成是一副机器,一旦有客观上可识别的疾病或功能障碍时,医师就会视病人为医疗介入的对象,包括使用最新药物、技术和外科手术等……在精神医学中,此方法背后怀着一种信念:透过准确识别客观的病变过程,就能成功诊断出精神障碍。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将概略介绍历史上「疯癫」概念,包括医学模式的发展。接着将探讨对该模式的一些主要批评,会引用到今日大量的相关文献,包括批判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以及心理健康服务使用者运动。本章最后一部分则提到,为何面对诸多批评,此领域的医学模式仍然继续形塑与主导我们对精神痛苦的理解和医疗措施。第一节疯癫的模式历史上,对「疯癫」的传统解释可以归为三大阵营:宗教、医学和心理社会(psychosocial)。一如所料,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今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亦然),宗教解释具宰制地位。例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国王扫罗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都冒犯了上帝,都受到惩罚而发疯了。在西方最古老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以及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剧作之中,有很多关于男女变疯的描述,通常大部分是来自上帝的命令。疯癫是「魔鬼附身」所引起的,这个观念最晚到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已出现,是由著名公众人物、卫理公会的创始人韦斯利所主张的。与宗教解释并存而又往往对立的疯癫概念,就是从身体或大脑寻找原因,这是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首先提出的观点。史考尔概括了该模式的重要元素:在希波克拉底医学的中心思想中,人体乃是一套系统,多种内在元素运行其中,它们彼此相互关联,也跟外在环境持续交互作用。此外,这套系统紧密地扣连在一起,即使是局部的病变,也可能影响到全体健康。根据这个理论,每个人都由四种互相争夺优势的元素构成:血液让身体变得湿热;黏液让身体变得湿寒,同时也形成无色的分泌物,像是汗水和泪水;黄胆汁或是胃液使身体变得燥热;黑胆汁则使身体变得燥寒,它起源于脾脏,让血液和粪便的颜色变黑。天生条件不同,所以这四种体液每个人的组成也比例不同,于是性情也不一样:血液供应充足让人乐观;黏液较多的人则苍白淡漠;胆汁过多的人会暴躁易怒。这些体液之间的平衡,可能受到内部因素(如饮食、睡眠不足或情绪纷乱)和外部因素(环境条件、战争)的影响而失衡,结果引致心智紊乱。在这种情况下,医师的任务就是透过诸如放血、催泻、呕吐等程序来恢复体液之间的平衡。这个模式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史考尔所说:这一套核心的疾病假设和治疗法,不只在希腊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更影响到罗马帝国,甚至在罗马灭亡、整套理论几乎从西欧消失殆尽后,还能在十和十一世纪时,再从阿拉伯世界重新传回来。从那时直至十九世纪初期,所谓的体液医学(尽管有些修正形式),在西方就成为难以撼动的正统自然主义疾病观,主宰了医学长达数百年之久。在剧作《疯狂乔治王》(后来曾改编成电影)中,班尼特生动地描述道,于十八世纪后期,如催泻、放血、呕吐甚至更可怕的生理疗法,仍然用于治疗所谓的精神疾病。相较于宗教理论上的解释,精神痛苦的体液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至少它声称是基于唯物主义/科学,而不是宗教,不会将疯癫视为上帝的某种惩罚,因而动摇与疯癫有关的污名。也就是说,体液理论经常受到宗教人士反对,又与宗教解释共存,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包括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会更为尖锐。例如,在宗教改革时期,伴随着整个欧洲大规模的猎巫行动,有五至十万名妇女被指控与魔鬼结盟或被魔鬼附身,遭受火刑或其他同样恐怖的方式而死在宗教迫害者手上。关于疯癫和心理健康的宰制观念,如同一般的统治思想,往往在政治和社会变革和动荡的时期受到挑战。在这时候,最进步的思想挑战最反动的观念。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时期。举例来说,欧洲许多女性一度被指控为女巫而遭到火刑,在这同一个社会,到了将近三百年前,佛洛伊德诞生和创立精神分析学说。在这个时期,社会开始采取人本观念,也就是说,疯癫的起源不是上帝干预或体液失衡,而是与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尤其是失落、痛苦、冲突和背叛。正如史考尔所观察到的,无论是悲剧或喜剧,疯癫是贯穿莎士比亚许多剧作的主题,例如在《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中,剧作家描绘「一个失常的疯癫世界,我们看到道德规范消失、人性被撕裂」。同时在《李尔王》中,疯癫变成自然现象:国王的疯癫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看似是因为受到寒风暴雨吹袭,但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一连串心理上的重创而崩溃:被自己的两个女儿背叛,了解到自己过去的愚昧和罪疚,最后还要对面三女寇蒂莉亚之死。我们后面将要看到,同样的人本立场也将成为挑战当前医学模式的核心观念。各种「疯癫」(思觉失调)和轻度精神痛苦都是根植于我们的失落感或受虐的生活经历。大约两个世纪之后,疯癫的宰制观念在另一个政治和社会动荡的伟大时期再次彻底地受到了挑战。罗伯特—弗勒里在一八七六年的著名画作《皮内尔使疯癫者自由》呈现了改革的一幕:精神科医师皮内尔于法国大革命前夕,在巴医院解开女性精神病患者的锁链,并将患者纳入因大革命而获得的人权保障范围。弗尔和西奥多?布朗提到:皮内尔与其同代人基于人本观念,要使精神疾病患者从牢笼之中释放出来,在改革后的精神病院中,彻底发展出新的「道德疗法」。这种解放使得医师与病患成为治疗上的盟友,患者的生活处境和社会环境在此关系中变得更为重要,否则他们以前都不被当人看,只是「疯子」和「疯女人」。在英格兰,图克和他的贵格会同仁在约克建立了精神病者的疗养院,他们所实践的「道德疗法」体现了同样的方法。此前,只有少数被视医院里。相反地,正如史考尔所说:与过去几个世纪一样,照护精神病患者的担子主要还是落在家人身上。基于低下阶层的贫穷和差劣的生活条件,患者家人也只能采取粗糙马虎的权宜之计。有些病人会被锁在阁楼、地窖或是房子外围建物之类的地方,完全称不上有什么值得羡慕之处。至于富裕的疯癫者(包括著名的萨德候爵),通常被供养在迅速增长的私人精神病院里,帕里-琼斯称为「心理疾病服务业」。法国大革命之后,道德疗法兴起,全国各地小型精神病院出现,使人们产生希望,要找到更人性对待精神痛苦的方法。然而,希望很快就破灭。正如皮尔格里姆和罗杰斯的评论:现实情况是,为贫民设立的精神病院与改革者的愿景相去甚远。一些疗养院试图复制基于道德疗法的制度,但它像其他医疗体系一样很快被抛弃了。就像济贫院(workhouse)一样,精神病院迅速成为「最后一线」的大型严密机构,然而这种定位就是一种污名。尽管精神病院由医疗人员经营,但他们未能提供治疗,违背了对精神失常者的医疗承诺。历史学家泰勒在她的著作《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举例提到这种医疗上的退步。她写下了个人的经历:一九八〇年代末米德医院关闭前,自己曾以患者身分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医院成立于一八五一年,那时人们叫它科尔尼哈奇精神病院:至少从设计概念上看,它展示了精神医学开明的一面,而不是阴沉的精神病院。美丽的园区和精心设计的建筑物立面……代表它是声望卓著的机构,目标是宽慰和治愈脱序的心灵。疯人院用锁炼和鞭子「管理」收容者,因而恶名昭彰。但现在这个具有典型维多利亚风格的精神病院,却让病友去工作。科尔尼哈奇像其他的精神病院一样,成为自给自足的社区,拥有自己的农场、果园、面包店和工作坊。在《国会法》的规定下,每郡都得设立精神病院,但正如泰勒所观察到的,就像许多其他精神病院一样,几十年下来,科尔尼哈奇已成为苦难和残破的代名词:十九世纪下半叶,精神病院的人口迅速增加。一贫如洗的患者从济贫院和临时收容室挤进来,精神病院「塞满了年久失修的疯子」。道德疗法在重重压力下失败了,除了收容者人满为患,原因还有「财务单位锱铢必较、院方管理者工作量太大、护理人员训练不足又没人监督」。到了一八六〇年代后期,大多数精神病院都恢复采用约束衣等身体拘束法。直到十九世纪末,精神病院改革先驱对于治愈病人的信心已完全消失,如同衰败的建筑物一样黯淡,遗传决定论取而代之,住在院里的心智失常者现今变为「退化」和有「缺陷」的人。照护沦为监护主义,精神病患者被视为「有污点的人」,精神病院成为了他们的监狱。泰勒笔下的精神病院经历,就如她在科尔尼哈奇的日子,浮现出一个更为普遍的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对于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民众,社会原本想供更人性化的治疗方法,但如书中所述,那些进步的观念和行动,都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力和筛选所颠覆、伤害和扭曲,甚至道德治疗也被当成是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人满为患是核心问题。一八二七年,英国精神病院平均每家收容了一百一十六名病人;到一九一〇年,数字变为一千零七十二人。从十九到二十世纪人数持续增长,甚至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每天关在英格兰和韦尔斯精神病院的病患平均约有十五万人。人数如此大规模增长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有三个因素尤为重要。首先,崛起的资产阶级(不仅在英国)决心要将那些能够工作和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分隔开来。无论是哪种机构,济贫院、监狱或者精神病院,都是资产阶级为此目的所找的「制度性解方」。正如史考尔早期著作《疯癫的博物馆》所述:精神病院能打造为具有威权结构的准军事单位,它似乎很适合用来培养劳动力的各种特性,包括树立「正当」的工作习惯,毕竟劳工总是特别想抗拒单调、规律和日复一日的工业化劳动。第二,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个人和家庭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在一八四四年的研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年轻的恩格斯绝佳地描绘出,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新世界中,男女劳工的生活如何被彻底颠覆。这段文字日久弥新: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穷人还被迫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里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忽而感到恐慌,忽而觉得有希望,像野兽一样地被追猎,不得安心,不得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激得他们不断投入其中,毕竟那是唯一能得到的享乐。如果他们挺过了这一切困难,那么也会失业,成为危机时期的牺牲者。这时,保留给他们不多的一点东西,也要全被剥夺。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家人又无法照护有心理问题的成员,想当然耳,很多任务人又都有酗酒和感染梅毒等状况,以上诸多因素都成为当时进入新精神病院的常见原因。在法国大革命后几十年,人们本来乐观地认为疯癫可以治愈,到了十九世纪末,终究被一种治疗悲观论所取代,人们开始将发疯等同于「人生宣判毁灭」,毫无片刻的希望。优生学论者也推波助澜,强调疯癫会遗传,尤其会影响工人阶级。著名神经学家西拉斯·米契尔在一八九四年对美国精神医学会的筹办者发表演说,他抨击这种悲观情绪,并斥责在场的医疗管理者,他称他们管理的病患为:一群行尸走肉、可悲的病人,就连怀抱希望的能力都失去了,坐成一排,迟钝到不会绝望,由护理员看着。沉默又阴森的机器人,只会吃跟睡、睡跟吃。第二节精神医学的恐怖历史这大约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在英国一所偌大的精神病院里,坐在前厅等待,那里住着的是在襁褓时收养我但患了失智症的养母。当我进入病房的时候,负责的护士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串钥匙,打开门进入一个大厅,里面一排排的床,其中一张难以辨认的,我养母正在那里躺着。钥匙在那条静默的走廊中叮当作响,我至今仍然容易回想起那个金属声,它代表了被漠视的一群人,在几个世纪里的重门深锁和没有希望的院舍之中回荡着。从有形的物质而言,锁具早已化为乌有,但在这些议题上,人的心智仍受禁锢而难以自解。塞奇威克的养母于一九五〇年代住在英国精神病院,与上文中米契尔的评论相较,塞奇威克的悲痛回忆更加凸显了,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心理健康问题患者得到的照护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米契尔所提到的治疗悲观论若真的存在,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更为明显。当然在这段时间内,主流精神医学的观念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例如,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受苦于「弹震症」(shell-shock,今天称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连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如诗人萨松也身受其害,这就足以反驳精神障碍的遗传理论,并支持另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弹震症可能是军人对恐怖战争的不自觉心理反应,而不是逃避战争的手段(当然,这并不能阻止三百多名英国士兵被当作逃兵遭受处决)。因此,少数精神医学家主张采用更人性化的应对方法,通常包括以谈话疗法取代先前残忍且具惩罚性的行为主义「治疗」。帕克?巴克在小说《重生》中,有力地描述这一时期精神医学的实践和辩论。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治疗师诸如马克斯韦尔?琼斯和比昂发展出更民主和集体的精神问题治疗法。例如琼斯医院或其他地方创立的团体治疗和治疗社区,以有意识的政治和治疗方法来应对一九三〇年代崛起的法西斯意识型态。然而,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精神医学家所采用的一些做法却非常落后,他们的工作方式会有意或无意地遵照自身统治阶级的意志。这里篇幅所限,不能充分讨论以「治疗」为名的残忍做法,它们通常主要实验在男女工人阶级身上,不过,我还是会举一些例子说明当时相关的氛围。上文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被迫重返战壕,当中精神医学扮演怎样的角色。士兵出现弹震症的各种症状,不愿再继续战斗,该如何处置,各方精神科医师彼此争论。史考尔逼真地描述了其中一种方法:不约而同,德国、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的精神科医师都利用强力的电流在病人身上触发巨大的痛苦,以迫使他们放弃症状,让哑吧说话、让聋子听见、让瘸子行走。德国医生中最有名的是考夫曼,是考夫曼疗法的发明人,他用强力而令人痛苦的电流去刺激病人瘫痪的肢体;治疗时一次会刺激好几个小时,同时大声喝令进行军事操练。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患者放弃对症状的依附,并且准备好可以重回杀戮战场。史考尔指出,令人震惊的是,考夫曼并不孤单,法国和英国的精神科医师「热切地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这主要是出自于军方上层的看法,无论这些医师是否有同情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各种规模的身体治疗法发展出来,但无论有意与否,对于深陷痛苦的个体来说,反而造成更大的折磨。其中包括蓄意令患者感染疟疾,以此治疗由梅毒引起的全身麻痹性痴呆;对患者进行手术(包括摘除器官),因为相信精神疾病根源于身体不同部位的慢性感染;胰岛素休克疗法;电痉挛疗法;广泛使用的精神外科手术,包括脑白质切除术和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术。到一九五一年,美国有超过一万八千名患者接受脑白质切除术。虽然以电痉挛疗法治疗忧郁症的有效性或其他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大部分这些残忍和有害的「治疗」,早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了。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yksmz.com/zzyhl/10820.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人人都会买,平常没少吃,这些常见食物竟会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