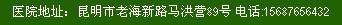|
中国国现代诗的第二大毛病是什么?当然是由生活化叙述的散漫导致的速度与频率缺失,但仅仅靠“加快节奏”四个字是解决不了的...... 毫无疑问,西方诗坛的后现代风潮对中国诗坛造成的冲击破也不都是负面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把叙述导入诗歌以来,中国诗歌的“身体肌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空洞的形而上修辞被生活化情节所取代,至少在阅读口感上显得质地饱满更具亲和力。但受时代调侃化、娱乐化小品文化的冲击和网络快节奏的更新速度所挤迫影响,其自由泛滥快速繁殖所导致的散漫性、粗鄙性缺点也被迅速放大了,若“本体模糊枝桠茂盛”是思辨性诗歌的主要缺点,那么,婆婆妈妈化、白开水化正日趋成为叙述时代的一般性特征。没错,从直观上来分析,这些缺点似乎都来自诗歌本体建构内在速度与频率的的缺失,由此导致诗性的降低,但若仅本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原则去提醒这些作者把节奏频率加快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换作另一体例或题材的诗歌这个病灶又将卷土重来。而且这种说辞也极易遭到作者的抵触和质疑,很简单呀,你说让人家把节奏加快,人家说我就喜欢慢节奏风格,你不喜欢可以去欣赏快节奏的呀。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个“快”和“慢”是无法通过一把尺子去量化的,到底多快才能合适?如何才能恰到好处?这就需要一把相对客观的“尺子”去测量并约束这种速度,方能被始作俑者所接受。 那么,这把具备相对客观性的“尺子”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诗力场”。 一、认识“诗力场” 类似戏子唱戏要有舞台,道士作法要有道场,诗歌中的意象要完成上天入地的戏剧化穿越,诗人也必须给它们安排一个特定的“时空隧道”来完成,这个特定的“时空隧道”就类似一面“魔镜”,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过去、未来、现在、天、地、人戏剧化交织一起的神秘世界,这面“魔镜”就是“诗力场”。所谓“诗力场”就是通过激活诗中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的隐秘关联,从而让一个群体产生互生互动的“社会关系”的“隐喻场”。如果把一首诗比作一个国,“诗力场”就类似这个国的疆域、法度、道德、风俗等的规定性,从呈现本体上来说,诗中的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身份”是对等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并且是时刻运动着的(天下没有“死人国”),而且必须受同一种“社会制度约束”——语境,这类似“溶液”的构成原理,溶液中的各种物质首先必须同被水溶解,其次必须互相运动,达不到一定互动速度便形成不了溶液。 在格律诗(此处“格律诗”为在广义上对格和律有相对要求的诗,非唐朝五、七律狭义称谓,以下同)时代,“格律”就类似“诗力场”的替代品,如对字数的严格限制,以及同类物象的对仗要求,就类似对诗中物象平等分封了疆域,而声律的要求,可视为同类物象“合唱”的制约,算作对这种“平等”的补充,至于对平仄的阴阳顿挫要求,就等于限制了物象同步的运动速度和节奏。这便如同形成了一个浇筑的模具,无论灌进去什么物质,都会在在这个模具规定下呈现出诗的特征。如刘墉和乾隆爷“合写”(也有人说作者是纪晓岚、郑板桥等)的一首咏雪诗: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皆不见。” 再比如,骆宾王的“咏鹅”诗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这些日常化俗语在格和律的约束下都成为了活泼俏皮的智性诗,但若去掉这个格律的“模具”变成自由体诗,这些“诗”便诗味索然了,要想把它们变成诗,需要重新构思重新组合,那么重新构思组合的依据是什么呢? 若根据以上的“溶液原理”把一首格律诗分作三部分,那应该就是:物象物象运动速度物象发声,这三点要求基本可确定诗力场的规定性。由于古诗词的主要社会公用更倾向于吟诵,而白话新诗则基本分成了朗诵诗和非朗诵诗两部分(也没有百分百的确定界限),除对朗诵诗部分可视作格律诗变体,继续延续格律诗的审美鉴赏要求外,对非朗诵诗的功用要求仅集中于“可感受”便可基本达成。那么,本文的立论就基本建立在“物象”和“物象运动速度”前两点上,至于声律,我的意见是,在不影响诗意溢出的前提下,可适当考虑声律的照应,但不必削足适履。 “诗力场”是区分诗与文的根本依据 为什么说诗力场”是区分诗与文的根本依据?首先诗与文是不同材料做成的“东西”,诗歌的主要构成材料是物或“物象关系”,即便诗中有人,在呈现本体上他也不是“社会人”,而是与其他万物结成对等隐喻关系的艺术化角色(大众文化层面的非艺术型诗歌除外);而小说或散文的构成本质是人或人与人的关系,除了童话、寓言、魔化小说等题材外,大部分还是以反映同宗社会现实为主。这便决定了它们诉求方式的不同:若文章的诉求是“以小见大”,诗歌就必须“以小折射大”,必须让主题产生“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弦外之音”,否则凭诗歌几行字几十行“小身体”的抒情效果,如何与文章的庞然大物相比?因此,如果小说、散文、随笔等文体系用稻草等有形之物把房间充满的话,那诗歌就必须用一枚烛火的光芒把房间填满,它对空间的占据必须达到一种“映照性”,方能体现同等存在价值。那么,如何才能把诗歌中的所有材料凝结成一个“发光体”,当然是“场化”,通过“诗力场”这个“阿修罗作坊”来进行“角色化”处理,否则,仅靠诗歌中的“人”去抒情,而其它物象不起作用,如何谈得上“发光体”的整体映照性呢? 那么,如何鉴定一首诗是有“场”还是无“场”呢,首先从主题来说,有“场”的诗整体就类似一个“意象”,它是立体的,具有整体的隐喻性与多维辐射性,而无“场”的诗是“平面体”或“意思体”,它只能反应与其同宗的社会现实,不能产生不可言说性。其次,从诗歌“身体构成”来说,有“场”之诗的“身体”类似溶液,诗中的物象都具有了复合意象性质,即便有独立意象出现,也是溶液作用下的质变结果,类似水流激起的浪花,它是有“根”的;而无“场”之诗的“身体”则类似线性的铺排,诗歌中的物象就是物象本身,即便有独立意象出现也是孤立的,由于借不上整体诗力场的助推力,全凭着作者即时的随机的感觉,大多时候必须和调侃性词语相黏连才勉强和整体发生联系,因而是做作的可笑的。 主题的映照性 什么是主题的映照性?简而言之,就是“仁者见仁的”,不同的读者都是一首诗能指的创造者我们拿两个例子比照一下便一目了然: 先看《人民文学》发表的一首诗: 《农村现状》 有力气的男人外出找钱去了才长大的姑娘被劳务输出了连长得一般的寡妇也进城给人擦皮鞋了老得掉牙齿的老家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孙辈白天在去年的土地上掰包谷夜晚守着三间瓦房和两声狗叫 再看一首网络诗: 《画面》 中山公园里,一张旧晨报被缓缓展开,阳光下独裁者,和平日,皮条客,监狱,乞丐,公务员,破折号,情侣星空,灾区,和尚,播音员安宁的栖息在同一平面上 年轻的母亲,把熟睡的婴儿,放在报纸的中央 前一首就是一首无“场”之诗,随机选取的一些写实事例,因为这些事件只能反映这些事件本身,这些人物、物象之间不能产生“化学反应”,因而不具有任何多维辐射的诗性,和一般的记叙文、段子没啥区别。你如果让它强制“影射”还麻烦了,比如,农民现在手里有钱了,不就因为经济承包责任制吗?让富余劳动力进城打工,那几亩薄地让老人、妇女、孩子播种就够了呀,中国毕竟不是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加拿大,难道再让他们再回到犄角旮旯喝西北风吗?而后一首则是一首有“场”之诗,“独裁者、和平日、皮条客、监狱、乞丐、公务员、破折号、情侣、星空、灾区,和尚,播音员”,这些看似没头没脑的杂乱无章的“大块头”“无厘头”,都被过期失效的“一张报纸”“场化”了,他们、它们都成为了同等隐喻身份的“角色”,他们、它们之间的关系每天都在被时代更新着,而他们的存在也都被时代自然选择着优胜劣汰着,因为“年轻的母亲,把熟睡的婴儿,放在报纸的中央”,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取代老朽不堪的旧事物不是必然吗?面对此诗,不同的读者心中自然有不同的“哈姆雷特”,因为在“诗力场”的约束下,这些人和物已经形成溶液混合成有机整体,甚至用“旧事物”、“新事物”两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就可代言此诗,那么无论把其置身于任何一个领域中,它的映射能力都是整体的有效的。而前首诗的可隐喻性只能建立在中国不合格编辑、评委、砖家、叫兽的笔下,比如他们会说,“狗叫”代表什么什么,掰苞米代表什么什么,但在让这些物代表什么的时候,前面那些人他就不管了。 物象必须“共溶” 诗歌中的物象必须建立在被同一个语境所约束下,才谈得上构成诗力场,才谈得上物象的运动速度,试问在一个灵堂中有人大笑有人大哭,那悼念的氛围还存在吗?同样的,在一场喜庆的婚礼上有人穿丧服有人穿红妆也自然是不伦不类。所谓“物象共溶”,是指诗歌中的物象在同一语境约束下,要么具有可互生互动的同质性,要么是表面无联系但具有可发生内在有机关联的“同芯”性,并不是随心所欲烂搭配一气。这种绝对自由状态的“胡乱配对”本应发生在初学者的“感觉体”中或写意识流小说或散文出身的“魔幻体”中才是正常,因为这是诗人由稚嫩走向成熟由外行变成内行必然要交的学费。但遗憾的是,目前此类诗歌都佩戴着先锋的护身符堂而皇之走进了最高级别的国家刊物,有的甚至获得了国家的最高诗歌奖项,不得不让人纳闷。若这就叫“先锋”,那所有的蝌蚪都可在被称作青蛙面前的先锋,所有的畸形人都可被称作正常人面前的先锋,如新近刚获得“人民文学奖”的一首诗: 《测量海》 龙王完全是错爱,给了把卷尺就让我去测量海从此我成了一个线人每天都踩着海岸线前进有时踩不巧踩到了海啸就会被一扔老远,远到了天边我只好用头罩当护照,劫持了飞碟再回到沙滩,像陈景润低着头走路撞倒了槟榔像亚里士多德,光着屁股思考把北冰洋当成了浴缸人类在后面继续添乱一会填海造田,用化肥渗透海面一会挖海底隧道,用人群冲开鱼群使我越来越像岳不群不仅乱了方寸,也忘了江湖的尺寸展开的卷尺缚住了自己的手脚像尸布,像黑幕,正好把乱码的生命裹住 这首诗就因为失去诗力场的约束,让作者陷入了词语游戏的绝对自由中,尽管这种无法凝结成“情节性”的后现代噱头被当作诗有些高抬,“被获奖”更是匪夷所思,我们还要耐着性子鉴定它的“场化”手段,否则就会被指作对此类体例的轻视。首先,诗中选取的意象和物象便不是同一语境中的东西,如“龙王”、“飞碟”、“陈景润”、“亚里士多德”等,既然你开篇第一句提到了“龙王”,便规定了后面与之发生关系的物象或意象应该是神话语境中的人物才算对等,比如孙悟空、哪吒等等,而不应是现代科技语境中的“飞碟”,因为这毕竟是魔幻现实主义诗歌而非魔幻主义小说,抒情性还是第一位的。那就让我们再宽容些,假定“龙王”、“飞碟”、“陈景润”、“亚里士多德”等堆在一起还算说得过去,那“岳不群”又是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的意象,因为前面部分属于历史公知人物或物象,具备隐喻的泛指性,但“岳不群”则是个狭义概念,仅仅属于武侠小说中的虚拟人物,和前面仍然不属于同级别的隐喻对象,强制安放进去不但导致抒情的语境丧失,也谈不上批判现实的疼痛感,最终沦为街头巷尾的轻佻笑话、荤段子、嬉皮士。有人也许会说,这本就是后现代的“荒诞剧场”不能拿正常诗歌的要求来衡量它,这也够不成宽容的理由,即便你要唱一出荒诞剧,也要在一个“荒诞场”的规定约束下才行,比如,你说“闯王和霸王分不清,张飞当了岳飞的兵”,可能有人鼓掌,但要改成“闯王和霸王分不清,张飞当了甲壳虫的兵”却不行,因为前一句已经为下一句规定了“场”,这些人物虽然胡乱搭配,但他们都是“同质性”的历史人物,但无缘无故冒出个“甲壳虫”,前面那句的“场”便作废了。 那就让我们再退一万步,假定《人民文学》的编辑和作者有此“无法无天”的特权,这些胡乱搭配的物件还算说得过去,那结尾的两句“展开的卷尺缚住了自己的手脚,像尸布,像黑幕,正好把乱码的生命裹住”极端内倾的深度隐喻又把前面的“嬉皮士”一棍子砸死了,难道一只“用头罩当护照,劫持飞碟”的荒诞鸟就该下出一枚“正好把乱码的生命裹住”文邹邹的“学院蛋”吗?!若前面部分的语境类似一个装神弄鬼的民间巫婆在大喊着“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那后面部分的语境就类似一个大家闺秀闭门娇吟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的诗也能发表获奖理由何在?唯一解释,这个刊物的编辑和评委是个傻蛋! 那我们再看一首同类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对照一下吧: 《母蝇》 韦白译 她坐在一株柳树上观望着部分的克雷西战场那些尖叫,那些呻吟,那些哀号,沉闷的践踏和倒塌。 在法国骑兵第十四次猛攻期间她和一只来自凡汀康特的有着棕色眼睛的公蝇交配。 她搓着她所有的腿坐在一只剖了膛的马身上沉思着苍蝇的不朽。 她稳稳地落在克莱弗公爵青灰的舌头上。 当寂静降临腐败的沙沙声轻轻地环绕着尸体 仅仅有几条胳膊和腿在树下抽搐, 她开始把她的卵产在皇家军械师约翰?乌尔的那只仅存的眼睛上。 就这样——她被一只雨燕吃掉了那雨燕刚从埃特雷的大火中逃离。 赫鲁伯从一只交配产卵的母蝇作为突破口,把一个血与火的战场弄成了“幽默产房”,因为整体处在一个魔幻的“童话场”约束下,把“剖了膛的马”、“克莱弗公爵的舌头”“皇家军械师约翰?乌尔的的独眼上。”“雨燕”等物象都整合到了一个“天平”上,由物象上升为了复合意象,因此,不但真实再现了战争的残酷场面,还越过现实的“现实性”抵达了“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就是把当下现实纳入历史现实和空间现实)——所有的战争,人民永远都是受害者,而受益者永远都是那些“苍蝇”,但由于苍蝇的本质是恶的,它必然也将被更大的战争受益者——雨燕所消灭,而雨燕呢,也必将恶有恶报——死于另一场战火…… 关于“物象必须共溶”的论断,本人在《论一首诗的身体性及身体权》、《提醒初学者注意的问题之三》等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二、速度或频率 如果把文章比作是一场竞走或长跑马拉松比赛,那诗歌更类似是一场百米跨栏或跳高、跳远比赛,尽管古有“文似看山不喜平”只说,但文章的波澜壮阔毕竟和诗歌的跳跃性、灵动性不可同日而语,它们的构成方式是源自两种截然不同的节奏,甚至可以说跟诗歌相比一切文章的节奏都是慢的。诗歌除了节奏的快还必须具备跳跃的灵动,类似跨栏或跳高、跳远比赛中的起跑加速跳跃再加速再跳越,最后那一跃更是惊天地泣鬼神般的震撼。只不过诗歌的加速与跳跃并非文章中的逻辑推导,它是靠意象、事像或物象关系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加速并不是就越快越好,它应该是在诗力场约束下力与美完美的契合。诗歌的速度分为两种物理速度和化学速度: 1,看得见的速度 所谓“看得见的速度”是指文字所指本身所体现出的物象或意象运行速度,或可称作是一种“物理速度”,只需通过词语转折或增加意象把叙述的节奏加快即可。 A,适当增加场景切换,便是提高速度。 对于叙述类诗歌而言,所谓呈现就是场景的呈现,若诗歌所指语义的递进仅靠叙述性情节的展开便消弭了与小说等文体的界限,因此加快场景的转换便如同提了速,如陈先发的《丹青见》: 《丹青见》 桤木,白松,榆树和水杉,高于接骨木,紫荆铁皮桂和香樟。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针叶林高于阔叶林,野杜仲高于乱蓬蓬的剑麻。如果湖水暗涨,柞木将高于紫檀。鸟鸣,一声接一声地溶化着。蛇的舌头如受电击,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中,窥见的桦树。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 以上这些不同时空状态下树木的陈列,形成了不同画面场景的直观对比,在最后一句“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牵引下,一步步加快,一步步跳跃,最后完成了惊天动地奋力一跃——生死不移其志的“丹青见”。 再比如辛波斯卡的诗《不期而遇》: 《不期而遇》(陈黎张芬龄译) 我们彼此客套寒暄,并说这是多年后难得的重逢。 我们的老虎啜饮牛奶。我们的鹰隼行走于地面。我们的鲨鱼溺毙水中。我们的野狼在开着的笼前打呵欠。 我们的毒蛇已褪尽闪电,猴子——灵感,孔雀——羽毛。蝙蝠——距今已久——已飞离我们发间。 在交谈中途我们哑然以对,无可奈何地微笑。我们的人无话可说。 中间部分(我们的老虎——已飞离我们发间。)的物象关系陈列,如同一组电影画面的蒙太奇切换,把作者对时代未来的担忧情绪渲染到极致,这种“退化”或“异化”不亚于一个原子弹爆炸溅起的废墟碎片,对读者的击打速度是比“风驰电掣”更快的。 B,增加意象,便是增加“跳跃” “盘峰论战”后,中国诗坛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象征意识流、伪叙述思辨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写作或学院派,一派是以日常叙事、反讽、魔幻等为主要手法的民间写作或口语派,按理,诗坛中的俄狄浦斯情节正是诗歌史更新换代的核心动力,但奇怪的是这两派都像跟意象有仇似的,前者用哲学、玄学的抽象思辨取代了意象,用词语转折直接完成意义转进,最终诗文不分;后者则干脆取缔了意象,直接“娓娓道来”唠唠叨叨,让读者急得只想吐血。这样,诗歌中的“跳跃”便形同虚设了,因为诗歌中的“意象”便形同寓意递进的“台阶”,站上一级台阶,便看见了一个神秘世界,这个“台阶”没有了,读者阅读你的作品便如同阅读“坐滑梯,根本不用停顿下来思考,刷的一下便过去了,相对长一点的则味同嚼蜡,枯燥乏味至极。因此,无论是叙述性还是非叙述性诗歌,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诗歌,都不该轻易放弃意象,它不但不是累赘,甚至是令诗歌快速抵达色香味的“味精”。 如特朗斯特罗姆的诗: 《果戈理》李笠译 夹克破旧,像一群饿狼脸,像一块大理石碎片坐在信堆里,坐在嘲笑和过失喧嚣的林中哦,心脏似一页纸吹过冷漠的过道 此刻,落日像狐狸悄悄走过这片土地瞬息点燃荒草天空充满了蹄角,天空下影子般的马车穿过父亲灯火辉煌的庄园 彼得堡和毁灭位于同一纬度(你从斜塔上看见)这身穿大衣的可怜虫像海蜇在冰冻的街巷漂游 这里,像往日被笑声的兽群围住他陷入饥饿的利爪但群兽早已走入高出树木生长的地带 人群摇晃的桌子看,外面,黑暗正烙着一条灵魂的银河登上你的火马车吧,离开这国家! 诗中“像一群饿狼的夹克”、“像大理石的脸”、“像树林的信堆”、“像狐狸的落日”、“像影子的马车”等等意象背后都潜藏着一个神秘世界,而这些“世界”之间只通过意象切换便“一步”便跨过来了,速度能不快吗? 也许有人会说,特朗斯特罗姆本来就是意象大师,主导风格便是深度意象,我们没他那么强大的修辞能力,只想在生活化的日常叙述中表达诗意,还需要意象吗?我像如意象安插得当同样增加叙述过程的可感受魅力。如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首生活化小诗: 《弗美尔的小女孩》(李以亮译) 弗美尔的小女孩,如今已经闻名望着我。一粒珍珠望着我。弗美尔的小女孩嘴唇红润,濡湿,而且闪亮。哦弗美尔的小女孩,哦珍珠,蓝头巾:你无处不明亮而我由阴影组成。光明俯视阴影带着宽容,或许还有一丝怜悯。 诗中就两个意象“珍珠”和“阴影”,便完成了两个“时空”的巨大跳跃,不但没成为此诗生活化的“负担”,反而成为点睛之笔,令它焕发出寓庄于谐俏皮生动的魅力。 C,通过制造转折和反差来增加“速度”。 所谓“速度”就是意义的转进速度,意象当然不是唯一“提速”的手段,因为“速度”的对岸是“意外性”,让这种“意外”更“意外”就是最有效的“提速”,如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可谓意外中的意外,那么制造度反差,无疑是一种最快的“速度”。 比如沃尔科特的《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文/德里克?沃尔科特(圣卢西亚)译/黄灿然我以水为生,独自一人。没有妻子和孩子。我竭尽一切可能要达到这点:阴沉的水边一所低矮的房子,窗子永远敞开着,朝向呆滞的大海。我们不会选择这样的东西,但我们是我们所造成的。我们受苦,岁月流逝,为了家庭的拖累,我们搬货,而不是搬我们的必需品。爱情是一块石头固定在海底,在阴沉的水下。现在,我对诗歌已无所求,但求真实的感觉,不要怜悯,不要名声,不要治疗。沉默的妻子,我们可以坐下来凝望大海,并且让这辈子淹没在碌碌无为和琐碎小事之中,活地像块岩石。我将忘掉感觉,忘掉我的才能。这要比那被看做生命的东西更伟大,也更艰难。 这首诗几乎没什么意象,通篇只有“爱情是一块石头”一句有意象,其余皆为平直的叙述,但它的转进速度却是惊人的,如这一段: 我以水为生,独自一人。没有妻子和孩子。我竭尽一切可能要达到这点: 诗中,“我以水为生,独自一人。没有妻子和孩子”看似不起眼的一句,其实暗藏玄机,因为下一句是“我竭尽一切可能,要达到这点”,这说明作者是有妻儿老小的,并非孤身一人,但为什么又“竭尽一切可能”做到这一点呢?难道作者是傻子?不愿意过正常人的生活吗?当然不是,作者当然是想做一个“裸体”进入诗歌艺术圣殿的纯粹之人,尽管作者写不出纯诗,但可以写出“纯粹”之诗。说实话,我是在阅读本诗遍之后才找到答案的,先前的多次阅读都蜻蜓点水般的滑过了,直到有一天儿子突然问我,“羊羔体”能获得鲁奖,爸爸你竟然赶不上一只羊羔吗?”,我才恍然大悟,没错,我始终对当今的获奖诗歌嗤之以鼻,认为早已远离他们的写作时代,但知道我写诗的父母、妻儿、朋友、博友并不知道这件事,我能把他们的看法全部抛开吗? 再看第二段反差: 我们搬货,而不是搬我们的必需品。爱情是一块石头固定在海底,在阴沉的水下。 我们整天忙忙碌碌为了什么?名义上是为了家人,但“爱情是一块石头,固定在海底”,却把妻子最为珍视的“爱情权”剥夺了,直到今天才意识到……,这既然为了妻儿而忙碌,而妻子却好像什么也没感觉到,这种痛难道不深刻吗?这种反差难道不巨大吗? 接下来的几段依然如是,貌似漫不经心实话实说,实际则是结尾一句“忘掉我的才能。这要比那被看做生命的东西更伟大,也更艰难”的巨大反差,所谓写出“纯粹之诗”就是纯粹地抵达生命的本真之地,那里可以尽情沐浴神恩,聆听神的教诲,因为神从来是不撒谎的,这便是“真、善、美”中“真”排在第一位的真正原因。 2,看不见的速度 看不见的速度多靠对表面看不出联系的物象或事像进行激活贯穿来实现,从而让诗力场焕发整体隐喻力量,因而此种提速时代比较类似于“诗力场”的“入场”手段,所谓“入场”就是导引全篇进入隐喻语境,所谓“隐喻语境”就是让诗歌中的所指部分产生了意外之意弦外之音,让作者与万物结成对等隐喻关系。 A,提笔起兴,势如破竹 这种入场办法比较类似于古人所言的“起兴”,但现代诗的起兴相比照古人的“顾左右而言他”的导引语势作用有了质的飞跃,它不但是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高潮、升华的制高点或画龙画虎的点睛之笔,因为与文章整体浑然一体不露声色,才闹出某些傻博士说西方诗歌“没兴”的笑话。 如,希尼的《挖掘》: 《挖掘》(袁可嘉译)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一支粗壮的笔躺着,舒适自在像一支枪。 我的窗下,一个清晰而粗厉的响声铁铲切进了砾石累累的土地:我爹在挖土。我向下望看到花坪间他正使劲的臀部弯下去,伸上来,二十年来穿过白薯垄有节奏地俯仰着,他在挖土。粗劣的靴子踩在铁铲上,长柄贴着膝头的内侧有力地撬动,他把表面一层厚土连根掀起,把铁铲发亮的一边深深埋下去,使新薯四散,我们捡在手中,爱它们又凉又硬的味儿。 说真的,这老头子使铁铲的巧劲就像他那老头子一样。 我爷爷土纳的泥沼地一天挖的泥炭比谁个都多。有一次我给他送去一瓶牛奶,用纸团松松地塞住瓶口。他直起腰喝了,马上又干开了,利索地把泥炭截短,切开,把土.撩过肩,为找好泥炭,一直向下,向下挖掘。白薯地的冷气,潮湿泥炭地的咯吱声、咕咕声,铁铲切进活薯根的短促声响在我头脑中回荡。但我可没有铁铲像他们那样去干。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那支粗壮的笔躺着。我要用它去挖掘。 起笔“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一支粗壮的笔躺着,舒适自在像一支枪。”一句便类似“起兴”把一些婆婆妈妈的生活化镜头导入了诗力场,从而把一把普普通通的铲子拔高到了“打天下的枪”同等高度,同时也把“用笔打天下”的细腻过程呈现得淋漓尽致,此处如“枪”之“笔”就是作者挖掘生活的“铲子”,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挖的越深收获越是丰硕。希尼为什么这么干?当然是为了出新,因为文人“用笔打天下”的说法已经被用烂了,同时在“笔”与“生活”之间的联系是直观的简单的,无法直接通过“打碎”的方式获得“呈现质感”,于是他采取了更隐秘的更遥远的暗喻手段,借助于“铲子挖土活动”的具体化、形象化,巧妙取代了用笔挖掘生活不易说、不可说的那部分。 不得不说,希尼是一位最谙生活化叙述技术处理之道的大师,一个寻常比喻做成的起兴,把一些针头线脑的琐碎小事轻描淡写地艺术化了,若不是采取这种“场化”结构,这首诗的素材不但不能上升到优秀诗作的高度,甚至连是否能被称作诗歌都难说。 B,巧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段,同样能达到强化抒情的“场化”效果 对诗歌而言,叙述永远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抵达抒情性的一种手段罢了,那么,在叙述中穿插设问、排比、描写等非叙述手法让叙述升华为抒情的“弹药”将会事半功倍。古诗中的对仗技术就类似一种“场化”技术,有很多句子本身不具有诗性,但两句并列便具有了“场化”功能,或者说由物象上升为了意象(复合意象),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等。白话新诗虽然不必讲究严格的对仗,但适当巧用相对统一的并列句式同样能消除唠叨过程的枯燥,达到“场化”效果,这对那些不顾读者感受一味我行我素的“埋头叙事者”无疑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如辛博斯卡《自杀者的房间》: 《自杀者的房间》 我敢说你们以为房间是空的。不对。房间里有三只靠背结实的椅子。一盏灯,足以击退黑暗一张桌子,桌子上一只钱包,几张报纸。一尊逍遥的菩萨和一尊忧郁的耶稣像七只幸运的大象,抽屉里一个记事本。你们以为我们的地址不在里头?没有书,没有画,没有唱片,你们以为?不对。一只小号优雅地握在一双黑手中。萨斯基雅和她热诚的小花朵欢乐,那神祗的火花架上的奥德修斯在第五歌的诸般冒险后在令人重获生命的睡梦中伸展四肢道德家们那组成他们名字的金质音节铭刻在上过硝的皮革书脊跟着他们的,是挺直了后背的政客们没有出口?房门怎么啦?没有风景?窗外别有景致眼镜就在窗台上一只苍蝇嗡嗡飞——就是说,还活着你们以为,至少会有一封信说明什么?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们根本没有信呢——而他原有那么多朋友,我们这些人恰好都可以装进靠在茶杯边上的那只空信封里。 这首诗几乎每段开头都以一句句式相对相近的设问:“我敢说你们以为房间是空的。不对。”,“没有书,没有画,没有唱片,你们以为?不对。”,“你们以为,至少会有一封信说明什么?但是,”,不但有效化解了叙述中的婆婆妈妈,令表达过程变得生动活泼,同时也把这些琐碎场景有效纳入了一个统一的抒情语境中,看似没用的废话,实则充当了看不见的“催化剂”作用,让读者可随时触摸到一种层次化的疼痛感。 再如策兰的《死亡赋格曲》:《死亡赋格曲》(罗池译) 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喝下它在傍晚我们喝下它在中午和早晨我们喝下它在夜里我们喝啊我们喝啊我们挖一个坟墓在空气里让你躺着不会太拥挤一个男人住在屋子里他摆弄他的毒蛇他写到他写到当天色黑到了德意志你金黄的头发玛格利特他写到这些然后走出门外群星都在闪烁他吹哨叫他的猎狗走近来他吹哨叫他的犹太佬排好队叫他们挖一个坟墓在泥地里他命令我们开始演奏要为舞会助兴 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喝下你在夜里我们喝下你在早晨和中午我们喝下你在傍晚我们喝啊我们喝啊一个男人住在屋子里他摆弄他的毒蛇他写到他写到当天色黑到了德意志你金黄的头发玛格利特你灰白的头发苏拉密斯我们挖一个坟墓在空气里让你躺着不会太拥挤他大声挖土深一点你们那边的你们其他的大声唱歌和演奏他抓住鞭子在他的皮带上他挥舞着它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你们的铲子挖深一点你们那边的你们其他的继续演奏要为舞会助兴 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喝下你在夜里我们喝下你在中午和早晨我们喝下你在傍晚我们喝啊我们喝啊一个男人住在屋子里你“金黄的头发玛格利特”你“灰白的头发苏拉密斯”摆弄他的毒蛇他大声演奏死亡更甜美一点死神是一个主人来自德意志他大声刮响你的琴弦更黑一点你会升起来然后随烟雾飘到天空你会得到一个坟墓在云朵里让你躺着不会太拥挤 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喝下你在夜里我们喝下你在中午死神是一个主人“来自”德意志我们喝下你在傍晚和早晨我们喝啊我们喝啊这死神是“一个主人来自德意志”他的眼睛颜色蓝幽幽他射你用子弹由铅制成他射你瞄准又命中一个男人住在屋子里你“金黄的头发玛格利特”他放出他的猎狗咬我们准许我们一个坟墓在空气里他摆弄着他的毒蛇和白日梦“死神是一个主人来自德意志”“你金黄的头发玛格利特”“你灰白的头发苏拉密斯” 每一段开头都有相同的一句隐喻“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喝下它……”,这些叠加的重复隐喻句便如同对叙述不断增加抒情性的加油站、充电机,把读者对纳粹集中营的厌恶与愤慨一步步推向极致,似乎听见了灾难的钢刀在受害者身体上咔嚓、咔嚓的剥削声。 再如沃尔科特的《仲夏》: 《仲夏》(节选)(飞白译)太阳把我的脸膛烧成了赤陶。脸把大阳窑的热度一直带进屋中。但我珍惜脸的皱纹犹如蓝的水纹。蚊呐围着锯齿形的仙人掌钻孔,熔炉烧得夹竹桃的刀叶全部卷刃,一根圆木,涂满了狂乱的符号。一座石屋在台阶上等。白的门廊在烧。告诉你海涛带给我的许诺吧:你格见到透明的诲伦走过,宛如阳光下的烛焰.沙地上的轻烟,朦胧而无影。我的手掌被纤绳切割,我拉这条船拉了四十多年。我的爱奥尼亚是烧焦的草的味道,是烤焦的桶柄吱嘎叫向铁锈的群岛;我爱的诗行里保留着全部节和疤。我等了整个昏晕的下午,热得没法思想,这陆中之诲的缪斯还在等待命名。而绷紧的地平线从这咸而暗的房里什么也捉不到。椅子出汗。纸弄皱地板。一只蜥蜴在墙上喘气 埃象锌一样闪亮。这时在门亮里:不是胜利女神在解凉鞋,是个姑娘在拍脚上的沙,一手扶着门框。 诗中“蚊呐围着锯齿形的仙人掌钻孔,/熔炉烧得夹竹桃的刀叶全部卷刃,/一根圆木,涂满了狂乱的符号。/一座石屋在台阶上等。/白的门廊在烧。”“阳光下的烛焰/沙地上的轻烟”,等对偶型排比都有效渲染了叙述过程的抒情气氛,让一首走着的诗迅速奔跑起来。 再如陈先发长诗《白头与过往》中的句子: 哦。老蟾蜍簇拥的冬青树。围着几个老头,吃掉了一根油条的冬青树。追不上有轨电车,骂骂咧咧的冬青树。穿着旧裤子,有点儿厌世的冬青树。焦头烂额的相对论,不能描述的冬青树。苦海一样远的冬青树。 尽管这些句子尚处在个人化主观语境中,并不太成熟甚至有些无厘头的“愣”,但却像几只狼激活羊群一样,把一首长诗拖拖拉拉的叙述过程有效激活了。 C,编筐重在收口,“尾句归场”一锤定音。 因自古以来就有“终篇决定价值”之说,因而尾句“入场”古今都比较常见(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类似歇后语的答案,有醍醐灌顶的警醒作用,令人恍然大悟经久难忘。而这句在技术上而言,就类似串糖葫芦的竹签,点豆腐的卤水,令前面的松散被一瞬间灌注成一体。如布洛茨基的《黑马》: 《黑马》(吴迪译)黑色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它无法与黑暗溶为一体。 在那个夜晚,我们坐在篝火旁边一匹黑色的马儿映入眼底。 我不记得比它更黑的物体。它的四脚黑如乌煤。它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周身黑咕隆咚,从鬃到尾。但它那没有鞍子的脊背上却是另外一种黑暗。它纹丝不动地伫立。仿佛沉睡酣酣。它蹄子上的黑暗令人胆战。 它浑身漆黑,感觉不到身影。如此漆黑,黑到了顶点。如此漆黑,仿佛处于针的内部。如此漆黑,就像子夜的黑暗。如此漆黑,如同它前方的树木。恰似肋骨间的凹陷的胸脯。恰似地窖深处的粮仓。我想:我们的体内是漆黑一团。 可它仍在我们眼前发黑!钟表上还只是子夜时分。它的腹股中笼罩着无底的黑暗。它一步也没有朝我们靠近。它的脊背已经辨认不清,明亮之斑没剩下一毫一丝。它的双眼白光一闪,像手指一弹。那瞳孔更是令人畏惧。 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它为何在我们中间停留?为何不从篝火旁边走开,驻足直到黎明降临的时候?为何呼吸着黑色的空气,把压坏的树枝弄得瑟瑟嗖嗖?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 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作者对一匹黑夜中的黑马反复渲染究竟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结尾的一句“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因为所有的话语权都掌握在黑夜的“黑手”之中,因而比他们更白的千里马是不允许存在的,即使有真正的千里马,也只能以比他们更黑的面目出现,那么,一个敢于与黑夜决裂的伯乐将是多么重要。 再如希尼的《铁路儿童》: 《铁路儿童》(黄灿然译)当我们爬上路堑的斜坡我们的眼睛便与电报杆上的白磁杯和咝咝发响的电线齐平。 像可爱的悠闲之手它们向东向西蜿蜒好几英里直到我们看不见,悬垂在它们被燕子压着的负荷之下。 我们很小并且自忖我们不知道那些值得知道的事。我们料想文字在电线上行走藏在那一小袋一小袋闪闪发亮的雨滴里, 每一袋都种子般装满了天上的光,生辉的句子,而我们相比之下是如此地无穷小 简直可以一下子穿过针眼。 作者对一串电线上的小水珠突然发生了兴趣,不厌其烦地描绘个不停,他究竟要干嘛?当然也是为了结尾的一句——“(我们)简直可以一下字穿过针眼”,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来说,那些小水滴就是一小个一小个的凸透镜或鱼眼镜头,能装下天下万物,我们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小不点,但作者真正想表达的却是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敬畏,只不过只有你把自己和万物位置放平才可发现自己的渺小,否则连这样“一行句子”都看不懂,还写什么诗?! 注,本文的“所指”系指物像关系的基本义,“能指”系文字背后的引申义,与索绪尔概念和音响形象来命名无任何关系。 白癜风网址长沙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yksmz.com/zzyhl/3610.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长期大量饮酒可引起酒精性脑萎缩和阿尔茨海
- 下一篇文章: 分享人工耳蜗技术临床进展